左宁南画像歌为柳敬亭作
何人踞坐戎帐中,宁南彻侯昆山公。手指抨弹出狮象,鼻息呼吸成虎熊。
帐前接席柳麻子,海内说书妙无比。长揖能令汉祖惊,摇头不道楚相死。
是时宁南大出师,江湘千里连军麾。每当按甲休兵日,更值椎牛飨士时。
夜营不喧角声止,高座张镫拂筵几。吹唇芒角生烛花,掉舌波澜沸江水。
宁南闻之须猬张,佽飞枥马俱腾骧。誓剜心肝奉天子,拚洒毫毛布战场。
秦灰烧残汉帜靡,呜呼宁南长已矣。时来将师长头角,运去英雄丧首尾。
倚天剑老亲身匣,垂毙犹兴晋阳甲。数升赤血喷余皇,万斛青蝇掩墙霎。
白衣残客哭江天,画像提携诉九泉。舌端有锷肠堪断,泣下无珠血可怜。
柳生柳生吾语尔,欲报恩门仗牙齿。凭将玉帐三年事,编作《金陀》一家史。
此时笑噱比传奇,他日应同汗竹垂。从来百战青磷血,不博三条红烛词。
千载沉埋国史传,院本弹词万人羡。盲翁负鼓赵家庄,宁南重为开生面。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东涧老人。学者称虞山先生。清初诗坛的盟主之一。常熟人。明史说他“至启、祯时,准北宋之矩矱” 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一甲三名进士,他是东林党的领袖之一,官至礼部侍郎,因与温体仁争权失败而被革职。在明末他作为东林党首领,已颇具影响。马士英、阮大铖在南京拥立福王,钱谦益依附之,为礼部尚书。后降清,仍为礼部侍郎。
猜您喜欢
陈浩然招游观音山,宴张氏楼。徐姬楚兰佐酒,以琵琶度曲。郯云台为之心醉。口占戏之。
春江暖涨桃花水。画舫珠帘,载酒东风里。四面青山青似洗,白云不断山中起。
过眼韶华浑有几。玉手佳人,笑把琶琶理。枉杀云台标内史,断肠只合江州死。
作者的其它诗文
推荐诗文
 钱谦益
钱谦益 左丘明
左丘明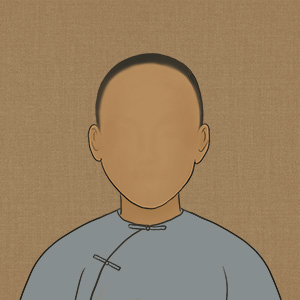 列御寇
列御寇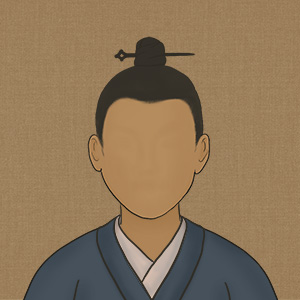 刘庭信
刘庭信 孙光宪
孙光宪 冯延巳
冯延巳 晏殊
晏殊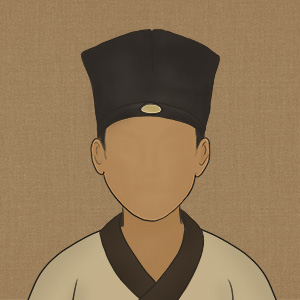 施绍莘
施绍莘 韦庄
韦庄 顾德辉
顾德辉 辛弃疾
辛弃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