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在京洛遇鸣皋游契甚洽一别五载鸣皋既赴召玉京余亦轗轲家难偶祝生如华携所业印正门下诗以勖之
昔余寓京华,红颜发垂腰。翩然遇祝生,里闬同游遨。
矫如长空鹤,清唳闻九皋。呻吟落珠贝,咳唾飞璚瑶。
奇情两突兀,衣被长飘飘。青箱破万卷,白眼持双螯。
调笑谪仙人,骑鲸堕烟霄。悲伤杜陵叟,二顷荒衡茅。
马迁下蚕室,相如困中消。东方枉设难,子云徒解嘲。
造物真小儿,役我随尘嚣。黄土抟下愚,茫茫若蟭蛲。
南阳贵宾客,什九横金貂。盗蹠葬东陵,高坟郁嶕峣。
伯夷饿西山,腐骨湮蓬蒿。陶朱窃西子,黄金压波涛。
屈原有何罪,委身饲鱼蛟。为善福安厝,为恶刑安逃。
长当毕吾愿,痛饮歌离骚。狂思捧北斗,醉欲呼天瓢。
玉女令鼓瑟,仙童使餔糟。穷年谇司命,真宰为嗷嗷。
以兹诉上帝,帝怒驰神飙。雷公击天鼓,屏翳嘘风潮。
青天拆龙剑,易水寒萧萧。吞声出京洛,洒泣沾河桥。
一与此生别,三年隔东郊。煌煌白玉楼,倏已升岧峣。
山阳怆邻笛,玉洞闻鸾箫。归来瀫川上,一室藏鹪鹩。
俗子遍阛阓,可人费招邀。尘埃闭穷巷,草色盈疏寮。
科头诵四部,赤脚翻缃缥。蟭螟鉴止足,偃鼠明逍遥。
皇天未悔祸,家门日煎熬。慈亲悴霜露,稚子埋山椒。
晨牝噪高堂,孽狐瞰林巢。戚戚类冯衍,皇皇逾孝标。
人生亦何乐,七尺徒烦劳。逝将弃家室,六合穷荒要。
翩然挟大鹏,九万腾扶摇。嗟咨念良友,宿草迷荒坳。
阳春慨永绝,白雪空长谣。欢言遘之子,兴文自垂髫。
飞扬慕古昔,跌宕扳贤豪。沾沾问奇字,片语为神交。
斯文久沦谢,玄阁长寥寥。尔志亮金石,遗风未全凋。
抽毫述往事,赠汝为虔刀。勖哉丈夫子,努力追前茅。
(1551—1602)明金华府兰溪人,字元瑞,号少室山人,更号石羊生。万历间举人,久不第。筑室山中,购书四万余卷,记诵淹博,多所撰著。曾携诗谒王世贞,为世贞激赏。有《少室山房类稿》、《少室山房笔丛》、《诗薮》。
碑者,悲也。古者悬而窆,用木。后人书之以表其功德,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汉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称矣。余之碑野庙也,非有政事功德可纪,直悲夫甿竭其力,以奉无名之土木而已矣!
瓯越间好事鬼,山椒水滨多淫祀。其庙貌有雄而毅、黝而硕者,则曰将军;有温而愿、晰而少者,则曰某郎;有媪而尊严者,则曰姥;有妇而容艳者,则曰姑。其居处则敞之以庭堂,峻之以陛级。左右老木,攒植森拱,萝茑翳于上,鸱鸮室其间。车马徒隶,丛杂怪状。甿作之,甿怖之,走畏恐后。大者椎牛;次者击豕,小不下犬鸡鱼菽之荐。牲酒之奠,缺于家可也,缺于神不可也。不朝懈怠,祸亦随作,耄孺畜牧栗栗然。疾病死丧,甿不曰适丁其时耶!而自惑其生,悉归之于神。
虽然,若以古言之,则戾;以今言之,则庶乎神之不足过也。何者?岂不以生能御大灾,捍大患,其死也则血良于生人。无名之土木不当与御灾捍患者为比,是戾于古也明矣。今之雄毅而硕者有之,温愿而少者有之,升阶级,坐堂筵,耳弦匏,口粱肉,载车马,拥徒隶者皆是也。解民之悬,清民之暍,未尝怵于胸中。民之当奉者,一日懈怠,则发悍吏,肆淫刑,驱之以就事,较神之祸福,孰为轻重哉?平居无事,指为贤良,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佪挠脆怯,颠踬窜踣,乞为囚虏之不暇。此乃缨弁言语之土木尔,又何责其真土木耶?故曰:以今言之,则庶乎神之不足过也。
既而为诗,以纪其末:土木其形,窃吾民之酒牲,固无以名;土木其智,窃吾君之禄位,如何可仪!禄位颀颀,酒牲甚微,神之享也,孰云其非!视吾之碑,知斯文之孔悲!
余年来观瀑屡矣,至峡江寺而意难决舍,则飞泉一亭为之也。
凡人之情,其目悦,其体不适,势不能久留。天台之瀑,离寺百步,雁宕瀑旁无寺。他若匡庐,若罗浮,若青田之石门,瀑未尝不奇,而游者皆暴日中,踞危崖,不得从容以观,如倾盖交,虽欢易别。
惟粤东峡山,高不过里许,而磴级纡曲,古松张覆,骄阳不炙。过石桥,有三奇树鼎足立,忽至半空,凝结为一。凡树皆根合而枝分,此独根分而枝合,奇已。
登山大半,飞瀑雷震,从空而下。瀑旁有室,即飞泉亭也。纵横丈馀,八窗明净,闭窗瀑闻,开窗瀑至。人可坐可卧,可箕踞,可偃仰,可放笔研,可瀹茗置饮,以人之逸,待水之劳,取九天银河,置几席间作玩。当时建此亭者,其仙乎!
僧澄波善弈,余命霞裳与之对枰。于是水声、棋声、松声、鸟声,参错并奏。顷之,又有曳杖声从云中来者,则老僧怀远抱诗集尺许,来索余序。于是吟咏之声又复大作。天籁人籁,合同而化。不图观瀑之娱,一至于斯,亭之功大矣!
坐久,日落,不得已下山,宿带玉堂。正对南山,云树蓊郁,中隔长江,风帆往来,妙无一人肯泊岸来此寺者。僧告余曰:“峡江寺俗名飞来寺。”余笑曰:“寺何能飞?惟他日余之魂梦或飞来耳!”僧曰:“无征不信。公爱之,何不记之!”余曰:“诺。”已遂述数行,一以自存,一以与僧。
 胡应麟
胡应麟 陆龟蒙
陆龟蒙 袁枚
袁枚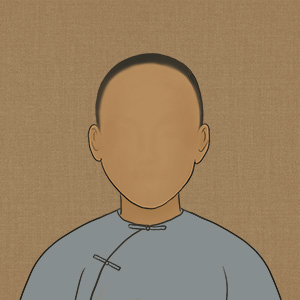 王国维
王国维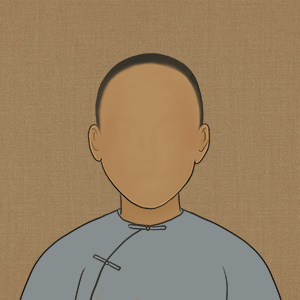 时彦
时彦 程垓
程垓 吴锡麒
吴锡麒 纳兰性德
纳兰性德 周邦彦
周邦彦 李好古
李好古